本文是因應《天橋上的魔術師 圖像版》出版所辦的講座〈我們的二次元世界--那些曾經影響過我們志願、美學與世界觀的作品〉所寫的心得,與談人有《天橋上的魔術師》原作者吳明益,以及兩位台灣漫畫家小莊與阮光民。本次的對談聚焦在動畫、漫畫如何影響這三位創作的人生觀、美學與未來工作選擇,很適合喜歡這些創作者以及喜歡漫畫的讀者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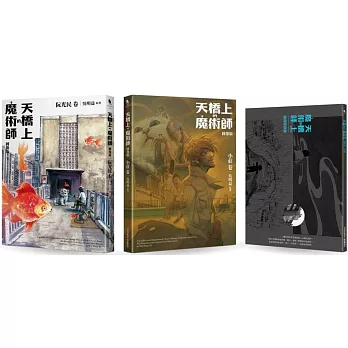
這次的三位講者都是我相當喜歡的創作者,很推薦大家去看小莊與阮光民的漫畫作品,台灣漫畫真的非常地棒!
主辦單位事後有提供三位講者的書單,相當精采,沒想到原來大家也是從小被漫畫浸潤的孩子呢!(聽完這場講座會不知不覺想買一堆漫畫)
本文將會以Q&A及大意的方式來呈現他們所談的內容。不過因為當天只是純筆記,內容可能有誤,也請大家見諒。另外書的連結我使用的是博客來的行銷策略聯盟連結,如果介意的話也可以自己搜尋書哦!
喜歡和漫畫相關的講座筆記的話,也可以看看這篇:
反抗的畫筆—香港反送中運動週年圖像展 講座:〈請按讚與分享-港人如何在無大台運動裡串連與發聲?〉筆記
我們的二次元世界--那些曾經影響過我們志願、美學與世界觀的作品
之所以會下這個標題,吳明益說,他覺得如果每次講座都是談自己的作品有多好多好,那就代表它可能不夠好;所以即使他發表新書,也都不太談自己的作品。這次因應《天橋上的魔術師 圖像版》出版,不如來談談別人的作品給了他們什麼養分。
這次的主題談論的是二次元(主持人:「小莊在事前還問我,『二次元指的是漫畫沒錯吧?』」)。主題談到漫畫對於他們人生的影響以及美學品味的培養,也呈現了現代「美學」變動的快速。

Q1:漫畫家曾是你的志願嗎?這個志願必然不是憑空出現的,如果要你舉出一至三部作品,影響了你對漫畫家這行的想像,你會想到哪些作品?為什麼?
Q1 小莊
小莊笑著說,小朋友才會說要以漫畫當志願。與其說他的志願是「漫畫家」,不如說他是以「圖像來敘事」做為自己的志願。他很喜歡這種用圖像來敘事、說話的習慣。
在以前漫畫審查制度的影響之下,台灣漫畫家沒有辦法自由創作,出版社選擇來進口(或翻版)日本的漫畫(如《小叮噹》、《怪醫秦博士》都是那些年代出來的產物);也因此,小莊以前看到的漫畫類型、風格都很單一。因為市面上流通的漫畫都是類似的內容,他一度認為所謂的漫畫是有一個「標準」在的;不過後來接觸到歐美的漫畫後,才發現原來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來圖像敘事,並沒有所謂的標準。
舉例來說,法國漫畫家Mœbius的科幻和奇幻風格、同時也是電影導演的Bilal、擅長畫情欲作品的Manara,都開啟了他創作的視野。
吳明益補充:美學是很容易被外在環境所限制住的。像是阮光民因為受日漫影響,加上台灣已經習慣日漫口味,所以相較之下大眾對他的作品接受度很高;而小莊因為比較偏向歐美的美學,似乎在台灣的讀者群接受度就沒有那麼高。
Q1 阮光民
阮光民說他小時候並不太知道「漫畫」這個詞,而是「畫卡通」或是台語說的「マンガ」;最早的啟蒙作品是《老夫子》。
喜歡畫畫,而且常會得到長輩的鼓勵,所以阮光民發現自己是擅長畫漫畫的。因為他的簡報上放了《小甜甜》,他也承認自己小時候也會畫少女漫畫;甚至當時開理髮店的三嬸婆常會請他畫小甜甜,再把畫作貼在理髮店的窗上當宣傳(阮光民:但他們都沒給我薪水啊)。
而以前看《萬里尋母》、《龍龍與忠狗》這些作品,阮光民雖然不知道自己到底為什麼哭,但也影響到他現在創作時都期待能夠做出「讓人感動」的作品。
Q1 吳明益
在場唯一不是漫畫家(但其實畫畫也相當強)的吳明益,小時候看《科學小飛俠》之類的作品也都會想要跟著描線、繪圖;不過他後來才知道,某種程度上畫風、美學都被當時的作品給限定住了。
直到後來他才發現,每種漫畫的題材都和他們的文化民族或歷史有關。例如日漫常常表現一種對於「少年」的迷戀,所以作品的主角大多是少年,大人都很廢;而「理想」的概念也常常出現在卡通歌之中。
歐美漫畫在早期的題材常常跟孤兒尋母有關,後來才發現這樣的故事設定與當時是大戰結束後有關係。
以前閒著沒事,吳明益也會跟著看漫畫週刊,他提到當時初次看到《JOJO的奇妙冒險》時印象深刻;因為這部作品的畫風很特別,故事又是吸血鬼的情節很不同於一般的題材;不過到後來,每個角色都有各式各樣的「替身」,而且每期都會跑出新的能力等等,到後來都會忘記之前的情節到底是什麼。

吳明益說,日漫作品顯示的是「外在規則」(即日本漫畫每集都有排名)激發的故事力。為了要衝排名,所以故事需要不斷推陳出新、每集都需要有新的刺激、新的能力,才能獲得讀者青睞。但這也讓他思索,畫家是真的在掌握故事?還是是被外在所限制出的故事?
《天才柳澤教授》這部很少人看過的作品,反而讓他對於漫畫故事有了新的想法。作品中的主角柳澤教授完全不同於過去的漫畫風格,題材也很特別(而且主角會讓他想起中央大學的孫致文以前都只走直線、睡前非得要把筆按照顏色排好才能入睡XD),反而讓他印象深刻,他才發現:原來漫畫的故事可以不只給孩子看。
因此,當2000年的作品《迷蝶誌》被詢問是否可以改編成漫畫時,他想著:或許這樣的作品可以改編成像《家栽植人》這樣類型的作品,每一集都以一種蝴蝶當成象徵(當然後來沒有改編啦)。
談到小時候的志願,他說他第一志願是當電影導演,第二是當漫畫家,但發現前兩個都做不來,最後才選擇當作家。
「為什麼不當漫畫家呢?」兩位漫畫家問吳明益;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天橋上的魔術師 圖像版》和小莊、阮光民合作大概花了五年的時間,但過程中他一直很想問編輯,兩位漫畫家到底有沒有先拿到錢呀?因為五年真的是一個很長久的創作歷程。(當然他後來沒問XD)
再加上,小說是以文字組成的,他在搭捷運、通勤時就能夠思索怎麼組織文字,但是漫畫每一格、每一格都需要花很多時間去思考分鏡,所以他覺得當漫畫家很困難。
Q2:漫畫在近代史裡的存在,是歐陸、美國與日本不同的系統演化出來的,雖然現在會互相影響,但它們的美學也大有不同。每個人的美學都建立在過去沉浸的美學裡,一樣的概念,如果要你舉出一至三部作品,它的美學影響了你的美學,你會想到哪些作品?為什麼?
Q2 阮光民
談到美學,阮光民認為其實人很難逃離出版社、大環境餵給大家的東西;尤其台灣社會受到日系漫畫風格很大的影響,也讓人不禁思考:市場是否只接受日本的漫畫風格呢?
阮光民提到了一些不同風格、美學的作品。像是鄭問的《阿鼻劍》、池上遼一這些漫畫家都呈現一種「定格之美」;《北斗神拳》也很有趣,作品的架構原先是受到西方《衝鋒飛車隊》(MAD MAX 2)所影響,劇中角色外觀設定多非日本原生所有,但這部它在日本火紅後居然又可以再傳到西方世界,是漫畫傳播很有趣的現象。而港漫的敘事方式比較像在說書,他們的漫畫生產結構分工細緻,更像是工廠式地生產。
至於他為什麼被日漫所吸引,是因為他日本有很多不同漫畫家,他們各自有著不同的繪畫風格及敘事方式,所以非常多元。
阮光民曾在他的自傳作品《阮是漫畫家》提到他在賴有賢漫畫工作室擔任助手的事情;在這次對談,他更進一步說,這段工作經驗對他的創作之路有很大的幫助。以前身為讀者,漫畫翻閱過去就結束了;但擔任漫畫助手後,他開始懂得怎麼去「看漫畫」。
Q2 小莊
小莊開門見山地說,其實影響美學判斷的不只是一部特定的作品而已,而是一連串的累積而成;風格,更是一個自我尋找的過程。不過他也分享了幾本近期的「養份」:
他認為井上雄彥對於人物的描繪特別地出色,每個劇中角色都很像電影中的人物一樣;繪畫風格非日本主流的松本大洋描繪人物卻非常精采,甚至每部作品使用的筆觸都不同;他尤其喜歡《竹光侍》這部作品;也提到《乒乓》常以廣角式的切換、不同筆觸的交替作畫,是有意識地在控制讀者閱讀的速度和方式。
接著,小莊提到法國漫畫家尼古拉·德魁西的作品《衝出冰河紀》。這位漫畫家的用色相當特別,加上他因為喜歡速寫的筆觸、覺得打稿的感受度和作畫方式最好,所以這種「不打草稿」的風格也成為他的標誌。
最後一位,則是擁有「漫畫界的小津安二郎」之稱的日本漫畫家谷口治郎。谷口治郎的作畫受到歐漫很大的影響,他相當刻意去刻畫畫中的背景,讓讀者忍不住停下來去慢慢端詳背景;這種作畫方式使得讀者會放慢閱讀速度,緩慢的步調讓他覺得相當有趣。
Q2 吳明益
接在小莊談谷口治郎之後,吳明益一拿起麥克風便忍不住說:當初他在看谷口治郎漫畫的時候也不禁思考,怎麼會有人想要畫這種題材、節奏這麼慢的漫畫!(不過我覺得這句驚嘆是讚美語氣XD)
吳明益提到的第一部漫畫作品,是矢口高雄的《天才小釣手》。他首先放出一幅《天才小釣手》的畫面,直嘆:這幅畫的構圖真的很美,即使掛在家裡也會覺得很開心;接著,他認為矢口高雄是很有文學性的創作,每一話都像一篇短篇小說,在短短篇幅就有極為精采的起承轉合,很令人感動。
《複眼人》這部作品,則是受到五十嵐大介和星野之宣的啟發。他認為寫小說很需要「空間感」,而五十嵐大介的作品非常有空間感。他也提到馮索瓦‧史奇頓一部描寫平行世界的《巨塔》,漫畫中每個場景的建築都巧妙到不行。
最後(我有點忘了怎麼接到這裡了),吳明益說,曾經有人問他在寫《單車失竊記》時,究竟寫戰爭的場景困難,還是描寫大象的心境比較困難?他笑著說,當然難的是前者啊!畢竟經歷過戰爭的人還在,要寫下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本來就比較困難,但大象的心境…誰會知道啊(全場笑)。
此時,主持人突然問了一個新的問題進來:
Q?:身為原作,吳明益喜歡這兩本被改編出來的漫畫嗎?
場上突然一片靜默,小莊和阮光民打趣地說,「不然我們先迴避一下好了。」全場觀眾看著吳明益拿起了麥克風,說:
我已經學會了,其實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表達意見的。
這好像真的挺適合接「語畢,哄堂大笑」的XD 確實台下的觀眾笑成一片。
事實上多次不同採訪及《天橋上的魔術師 圖像版》附贈別冊中都約略看得出來,吳明益一開始對於自己作品要改成圖像版,是有些要求和想法的;不過在多次與阮光民的磨合和討論後,他也漸漸放手讓他們去自由發揮這部作品。
吳明益說,在作品被翻譯後,他開始認知到自己並沒有那麼優秀,畢竟他不可能知道他被翻譯出來的作品到底是好是壞;因此,既然要做,就要完全相信合作夥伴的能力。
他也說,近幾年來他也漸漸不對新的創作者提出評論與看法,因為:
二十年後我的美學可能就消失了,新的美學觀念會再上來。既然如此,我又憑什麼去指點別人呢?
Q3:或許從我們這代開始,可能下一代會更鮮明,我們的世界觀或人生觀,不見得是那些「經典」所建立的。比方說就學時曾經被灌輸的世界觀與人生觀,很快在我讀到一些文學作品後被挑戰,然後瓦解。是否曾經有些漫畫,正面、或潛在地影響你的世界觀,在很久以後你回頭才發現這樣的事實?
Q3 吳明益
吳明益提到,有一次他去日本玩,發現很多店家都有貼上《小拳王》的畫作,那次的經驗讓他思考:如果一部作品、一個人物的形象能夠如此活在大家的心中,那真的就令人滿足了。雖然《小拳王》這作品中有很多「中二而美好的哲學」,但它的結局「他已經燃燒殆盡了」真的很迷人。
另一個影響吳明益的作品,則是《娃娃看天下》或大家更常聽到的「瑪法達(Mafalda)」(這部作品因由三毛翻譯,在當時非常有名)。吳明益回憶,這部作品以異於台灣的角度來看世界大事,也包含了政治諷刺的段落,是一種「用輕去承載重」的方式,讓他印象非常深刻。
常被人稱為神作的浦澤直樹《MONSTER》,吳明益也稱讚它有好幾層不同的故事結構,除了每個角色自己的視角、自己的故事軸線外,連繪本也獨立成一個故事,建構出一個很完整的世界觀;「那句『我體內的怪物已經長得這麼大了』多經典啊。」
Q3 阮光民
阮光民以前一直在思考自己到底要畫怎麼樣的故事;而谷口治郎《遙遠的小鎮》,便是他創作的人生轉捩點。以前看的漫畫很常塑造主角有多強、或是經過鍛練之後變得多厲害,但這本漫畫描寫的卻是一個大叔的靈魂回到過去的故事。「明明是一個如此無聊的故事,卻也可以成為一個故事!」從此之後,他知道原來想畫的其實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這部作品也讓他體悟到,漫畫家就像是電影導演,只是他們不是用長鏡頭,而可以用字數、圖像刻畫它的深度,來影響讀者的閱讀速度和焦點,讓他們可以在一個畫面駐足許久。
另外兩部作品則是井上雄彥《浪人劍客》,以及松本大洋的《Sunny》。前者呈現作者步調漸漸慢下來、體現自身哲學觀的作品,後者主角自身成長的故事讓他印象深刻。
Q3 小莊
「這題…我好像也沒有什麼世界觀啦。」小莊這樣說。不過,星野之宣的作品很早就開啟了他對於世界的想像。他說,當時很多人看了諾蘭的《星際效應》很感動於那樣的宇宙世界,但他很早就從漫畫感受到這樣的世界觀了。
小莊並不太喜歡像是偶像劇般的故事,因為他知道世上完美的人太少,不完美的人反而更貼近一般人。
其他的作品,他提到了我們過去常只知道藤子‧F‧不二雄的《哆啦A夢》,但他也很會畫科幻作品,如《SF短篇集》他在家收集了一整套。之前提到Mœbius的《貓之眼》甚至給了小莊靈感,畫了《窗》這部作品。
他另外介紹了Thomas Ott的《R.I.P: Best of 1985-2004》這部描寫人性黑暗面的作品;但他最懾服的是,全書的白色線條居然是作者用筆刀刮除黑色紙張而成的(可見以下影片);這樣富有特色的創作也影響了小莊的《80年代世件簿》(只是他並沒有那麼費工刮紙就是)。
Q&A時間
小莊回答完後,整場活動算是結束;不過舉辦方(或說吳明益)提供了Slido問卷讓大家提問,這場居然很佛心地讓三位回答了大多數的問題。這裡,也列下幾個我覺得有趣的Q&A來跟大家分享。
Q:想請問兩位繪者,在創作本書漫畫版時,出版社或吳老師有對畫面或角色的呈現,提出任何要求、修改或希望事項嗎?還是完全交由繪者自由發揮呢?
阮光民說他在2015年接下了《天橋上的魔術師 圖像版》之後,一開始只要每畫十頁就會拍給吳明益看、問他的意見。吳明益笑著說,在合作的初期,他當時還曾經不好意思地希望阮光民能用小說的文字來當作對話及旁白,因為他原本想要留著文字的靈魂(阮光民:我不知道可以用他小說文字啊!我以為都要重新自己來欸!)不過後來溝通後,改成心境或比較抽象的部分用小說的文字,對白則由阮光民自由發揮。
小莊聽完在旁邊笑著說:
我很早就學到了,沒事不要去問客戶問題。
小莊在阮光民之後才接下改編,他說吳明益已被阮光民「磨練」了,因此不太擔心和吳明益合作,但他擔心的是:「萬一合作中間磨合出了些什麼問題,我可能會失去一個偶像(吳)」以及「原有書迷的期待會不會落空」。
Q:在選擇漫畫天橋上的魔術師時會刻意跳過較情色的部份,為了讓出版較容易被市場接受嗎?也想問吳明益老師在寫作時如何跳脫出教授身份,而把想寫的情境無論粗俗情色的部分,都能寫實的表現出來
這題一問出來,小莊馬上表示:「情色的部分都被阮光民挑走了。」(全場笑)
吳明益說,之前書一出,就有讀者詢問:既然這是一部描寫童年的作品,為什麼要有那麼多情色的故事?拿掉應該比較好吧?不過若還原當時中華商場的居住環境,聽到隔壁鄰居在做愛的聲音是很習以為常的事,所以他們性啟蒙其實是很早的;更何況「性」本來就是人很自然的事情,為什麼該拿掉呢?甚至吳明益後來還叫阮光民多畫些成人的畫面(阮光民:他叫我多畫一點!多畫一點!)
Q:發問者是行動矮子,行動緩慢到中華商場拆了我都還來不及出生,所以想請問老師們如何透過文字或圖像讓不同時代的讀者投射感情到這樣的作品中呢?
阮光民不是台北人,他本來就沒有經歷過中華商場(也不確定小時候自己有沒有去過);不過即使如此,他還記得第一次讀小說時,光看文字就能用想像力拼湊出中華商場的樣貌。
小莊則是曾經經歷過中華商場輝煌的時代,因此在畫作中是相當努力去重現這個地方的;不過他認為作品投射的情感應該是在人物上面,而非中華商場這棟建築。
吳明益則說,像是他的作品被翻譯到國外(如法國),這些海外讀者不但不認識中華商場,甚至可能連台灣在哪裡都沒有概念;不過,他們仍然可以透過聯想來想像這故事的場景。「人是一種富有想像力的生物,有能力去建構虛擬的場景」。所以他並不理會讀者會想什麼,只是自己會很努力研究資料,來重現這樣的背景。
Q:阮光民老師的作品中,每個故事主角的童年,都會相互串場,想請問老師,這是刻意安排的嗎?
「是」,阮光民回答。雖然小說中每個故事都是獨立的,但他想像大家既然生活在這樣的地方,可能都是鄰居或認識的人,所以就把他們放在同一個舞台上來表現這些故事。
Q:很喜歡小莊老師的《九十九樓》,特別是最後一頁,讓我印象深刻。很好奇老師為什麼會選擇那樣呈現?
因為最後一頁是小說情緒的收尾,所以他刻意這樣去安排。根據他的童年經驗,有時候雖然不一定會親眼看見事情發生,但想像力可能會讓你更有身歷其境的感覺。因此雖然小說篇幅寫的不多,但在改編時他刻意安排了不少的畫面。
Q:吳老師,請問您對於天橋上的魔術師連續劇,有著什麼樣的期待?
那天台下也坐著連續劇的負責人,吳明益說「我自己沒有期待」,因為他是全程相信這些人更加地專業;但是他的母親曾經在飯局提到這件事,甚至還說,自己現在還活著就是為了看這部劇(台下一片驚呼)。
不過他說沒期待,還是很期待楊雅喆會創造出什麼樣的《天橋上的魔術師》。
Q:感覺三位老師的興趣志向很早就顯現,這對求學過程有何影響嗎?請問明益、小莊、光民老師贊成喜歡繪畫的孩子在國中、高中時期就進入美術專班嗎?
三位與談人都一致地說,讓孩子自己決定吧。
吳明益更說,他一直以來都是做父母反對的事情。與其像他做什麼都瞞著父母(他以前甚至會一夜沒睡,偷偷出去拍片),如果發生了什麼遺憾的事可能後悔都來不及,倒不如好好的讓孩子自己去找尋自己的興趣。
Q:從書籍封面的設計也可以看出針對不同國家讀者而有不同選擇,我很好奇向來在作品封面使用自己設計的圖像作品的吳明益老師,為何日文版的封面與中文版和法文版用了老師自己的設計不同,而選用了一張中華商場的老照片呢?有針對日本讀者市場考量?或是照片本身有其意義?
吳明益一樣說,相信他們專業;這些行銷的人一定都比他懂,所以就交給他們去做,「不要以為作者自己像宇宙一樣大。」
Q:老師若得到諾貝爾文學獎,您認為評審持的論點是什麼?
「我不可能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吳明益說,「如果我得了,那就是評審的失職。」
他進一步解釋,如果有關注世界的文學作品的話,就會發現有太多優秀的作家和作品了;以他現在的才華只可能往下坡(吳明益:你們想想,有哪位作家的顛峰在七十歲嗎?一定是像我這樣的年紀),如果有一天他得獎了,只有可能是他在多年後寫出了遠超出他現有能力的作品。
(主持人:我以為你會一句話就結束這個問題。)
Q:問阮光民老師,第一話裡面最後有一位戴眼鏡的男孩,是用吳明益老師的形象去畫的嗎?
問這題之前,主持人要求阮光民只能用YES/NO回答這問題。
聽完後阮光民愣了一下,說「哪一位啊?」主持人:「阮光民可能不記得了?」阮光民:「是最後尿尿的那位嗎?那……是。」(全場笑)
Q:要如何知道吳老師的演講訊息?
吳明益在去年四月宣布離開臉書,就此大家漸漸難以掌握他的演講訊息。他說他覺得創作者都是玻璃心,在有臉書的情況下可能都會關心自己的追踪人數、按讚人數等等。他也發現,過去用臉書,常會有一樣的人一直去參加他的活動,但他覺得人再怎麼能講,還是會講到一樣的事;與其相互厭倦,不如讓他面對一些新的人吧。
「相見就是有緣。」
Q:想問明益老師,透過不同媒介接收到的感動對你來說有甚麼不同的意義或之間的差異嗎?最終選擇站定在文字這塊,並且從此嘗試各種跨域,這一路上有甚麼想法的改變嗎?無論是電影、圖像、遊戲、音樂、戲劇,各式吸睛的敘事中,文學有什麼樣的特點與其抗衡呢?
受限於時間的關係,吳明益很簡單地說,文學就是由文字所組成的。文字很難改變,但語法是會改變的。以前很多人笑火星文,但實際上這是一種很有生命的語言呢!
他也提到語言學家說(語言學界:感動),語言可能三十年就會有很大的改變,因此像那些穿越的作品幾乎不可能溝通啊XD
他能告訴創作者的,就是要去擁抱這樣的語言變化,文學不要再用老的修辭了,要用新的方式來表現。不過他也說,自己沒有做到是因為自己已經老了,越來越難吸收這樣的新事物,但呼應了最前面一開始談的「美感」變化,他告訴大家:
不要執著某個特別的美感,美感會一直變的。
感謝收看:D
如果您喜歡本篇文章,請幫我在下方的「拍手區」按圓圈圈裡的拍手圖案5次吧:D
您的舉手之勞,可以讓我得到 Likecoin 的回饋哦!
只要註冊/登入帳號(支援Facebook、Google帳號,註冊不超過1分鐘),只要替我按五次拍手,您不用支付任何費用,卻能給予我最大的鼓勵,讓我寫出更多的好文章哦!



